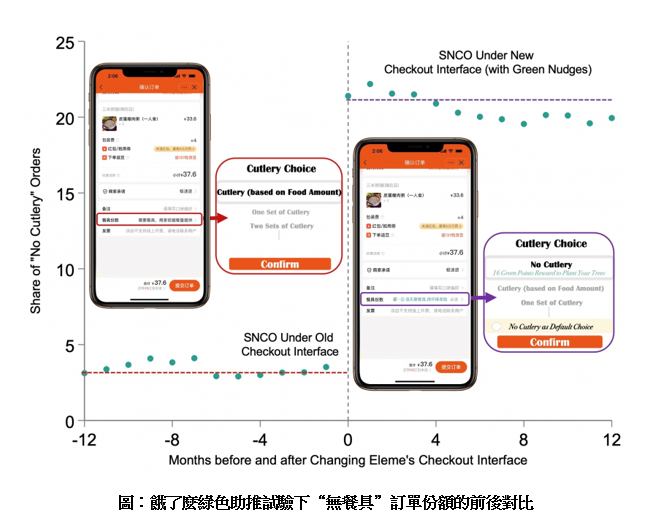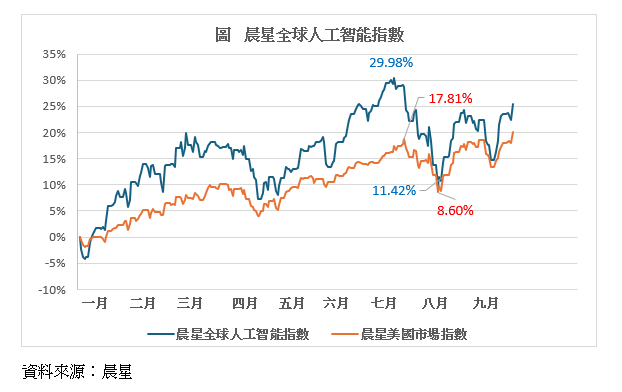美國大選結果折射出的避責文化
互相指摘或卸責,也許只是個人沒擔當的怯懦行為,但放大到社會層面,就足以產生混淆公眾視聽的惡果。政治人物往往透過彼此指摘來轉移視線,力求貶低對手而抬高自己。在競爭白熱化的選舉中,不惜一切推卸責任已成政客的慣技,或對選舉結果以至未來管治和政策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
民主黨敗選背後
本月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共和黨特朗普以壓倒性姿態勝出。賀錦麗慘敗後,其所屬民主黨內隨即出現大舉卸責現象,矛頭直指拜登,歸咎他未能及時退選,陷賀錦麗於尷尬境地。不少黨內成員亦認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選民歡迎,雖然他及後宣布退選,賀錦麗仍因受選民支持度不足,未能於明年入主白宮。
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改選中失去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較4年前表現更糟。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總統以來,美國3100多個縣的選民大都轉向右傾。民主黨向來標榜的支持墮胎權和民主立場,無法像經濟和移民等迫切議題引起選民共鳴。
儘管美國失業率現正維持在歷史低位,股市暢旺,但物價高、房租貴也是事實。拜登任內,物價上漲超過20%。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指出,各種經濟指標之中,通脹對政治影響最大。一般人無需數據,也對通脹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在今年舉行選舉的10個國家中,執政黨的表現都不如上屆選舉,相信也與高通脹有關。
根據民調,三分之二的美國選民對經濟給予劣評,收入較低的一群傾向於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個百分點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萬至10萬的選民,但在這次選舉中卻逆轉獲勝。民主黨人似乎忽略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財務穩健和身心健康)必須先行,然後再滿足其他方面。在競選活動中,民主黨聚焦於民主等議題而忽略經濟。曾經是該黨核心的工人階級選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來愈多人按自身的經濟利益來投票。黨內對敗選結果莫衷一是,更出現互相指摘。如此反應,是否就能把選票贏回來?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倆層出不窮,皆因政黨或領導人藉此進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權在握。
企業卸責文化
在商業環境中,互相指摘確也頗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臨存亡危機,責任的分配將直接影響其股價和投資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層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徵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難逃衰敗的厄運。從管理學的研究可見,將公司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的管理層,其整體表現往往不及承認自身責任並自我反省的公司。在瀕臨破產的企業中,可以看到不少經理將業績欠佳委過於其他部門。相反,管理層若有責任感,則有可能轉虧為盈,讓業務重上軌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汲取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長風險規避文化,員工因害怕受責備而不敢主動行事,或礙於不願分享想法而窒礙創意。眾所周知,成功的企業有賴暢順的運作;管理層必須致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解決公司內部的分歧。
「無過失」調查的啟示
反觀一些行業早已認識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業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環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於「無過失」調查的程序。在美國,負責調查有關事故的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明確表示,調查目的並非追究責任,而是找出問題並提出建議,以防同類事件重演。航空業不進行追責的事後調查,為現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這種調查方式有助於建立開放的安全文化,鼓勵業界報憂,最終目的是確保減少意外事故。英國的航空監管機構在誠實錯誤和其他錯誤之間劃界線,也是個好的起點。航空公司致力於營造一種文化,使機師不會因為與其經驗和培訓相符的決定或疏忽而受到懲罰。這種做法並非完全免責,只是將責任範圍收窄而已。
醫療保健領域也面臨類似情況。一旦發生醫療事故,世界各地對病人的補償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國依賴找出過失的訴訟程序,而紐西蘭則是全球最早實施醫療事故處理制度的國家。紐西蘭率先以「無過失補償」的程序來處理醫療事故,並於1974年成立意外補償局負責,接受因工作、交通或醫療事故導致的傷害賠償申請。在這一制度下,無論醫療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傷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補償局提出申請。只要問題與醫療診斷或決策相關,申請便可獲批准。該制度推行後,除非醫療人員的行為嚴重違法,否則紐西蘭患者幾乎無法向醫療機構提出訴訟。
在航空和醫療領域,從錯誤中學習的動機特強,因為從業員在工作中生命隨時受到威脅,安全無疑至關重要。因此,軟件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經常進行「無過失的事後分析」,以調查網站失靈或伺服器故障等問題。一般人不易理解這種不追責的思維,心理學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為此提出一個框架,以釋除大眾對無能和犯錯者逃避責罰的疑慮。
問責而非卸責
要逃避指摘其實並非易事。一、當事人為了避責往往要大費心力,但指摘別人反而是毫不費力的快速反應,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於記錄錯誤並確保流程得以改進,則難免涉及結構性的變化。例如無過失事後分析長期以來已屬谷歌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該公司為此提供模板、反饋和討論小組。二、企業管理層既然大權在握,指摘屬下僱員也就輕而易舉。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最近合作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指出當權者往往認為其他人會將失敗歸咎於他們。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主管或工人,然後檢視有關錯誤的紀錄。參與者都收到道歉信,聲明網絡連接不穩定,以致任務無法正常完成。結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認定抄寫員應為失誤負責,主張剋扣其報酬。由此可見掌權與施罰之間的因果關係。
指摘別人似乎也具傳染性。2009年,心理學學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發表合著論文【註】,其中一個實驗要求參與者閱讀有關政治失敗的新聞,然後寫下政客的過失。讀到關於政客將失敗歸咎於特殊利益的報道時,參與者更可能將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卸給別人。至於讀到政客承擔責任的參與者,則更可能肯為自身的不足負責。同理,管理高層若輕易指摘別人,公司員工也會有樣學樣。如此一來,不難衍生出一種推卸責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對於失責和指摘的容忍度不盡相同。例如集體主義可能導致共同指摘,而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人指摘則較常見。相互指摘的經濟學強調人類行為與經濟結果之間的相互作用。了解這些動態關係當有助於機構創造出更具建設性的環境,減少諉過於人,以鼓勵問責和合作。
註: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