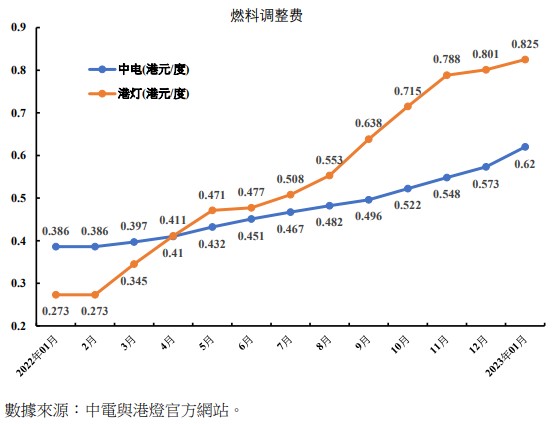停滞不前的拉丁美洲经济
最近两宗有关足球运动的新闻,大概受到不少球迷关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为主力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在两周前第三度赢得世界杯,16年后再将大力神杯从欧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为巴西三夺世界杯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离世。对一些香港人来说,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联想;对南美洲、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来说,足球是国家的骄傲;对当地很多青少年来说,足球是个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运动的蓬勃,或许掩盖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现实。
为方便讨论,这里将南美洲扩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为一个区域列出。按有关资料,这地区在2021年占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于全球的平均值。
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增加生产和收入,发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国家(如美国)的水平为指标,即有没有与后者「趋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为指标,以购买力恒等的汇率来计算,拉美经济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注】的数据,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6%,但随后一直低于30%,在上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这个比例没有改变,不等于没有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步伐与美国相同,没有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个比例下跌,则表示与美国的经济距离愈来愈远。还好,拉美经济在本世纪有些少好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该区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为升至美国的25%水平。
阿根廷堕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个国家,它们的经济表现自然有一定的参差,但总的来说,除了个别几个国家之外,人均收入与美国水平相比,多年来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经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国家,从十九世纪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经济大萧条后,阿根廷的经济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国比较逐步下跌,最近几十年都在美国的30%上下,没有什么进步,可以说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显例子。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国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国的40%,随后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后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经济发展有一段特别的插曲,就是社会党在1970年选举获胜,领导人阿连德(Allende)成为智利第28任总统,是拉丁美洲首位通过民选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上任后实施企业国有化及价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国的后院搞社会主义,自然不容于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幕后策划和协助,智利军人皮诺契特(Pinochet)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并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
皮诺契特上台后重用一些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者主理经济事务,后者被统称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众所周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导思想为自由市场,政府在经济活动的角色应减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经济政策在数年内出现了180度的改变。
由阿连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诺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比较,主要趋势都是下降。在军政府统治期间,一方面市场是开放了,但另一方面,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愈趋严重,很多以前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关的人手上。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没有很快的推动经济,要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智利的经济才拾级而上,成为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亚太人均收入追贴美国
和拉丁美洲不同,亚太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持续上升,也就是愈来愈追上美国的水平。以亚洲四小龙为例,四个经济体合起来计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达到美国的12%,但到2012年已经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经和美国差不多,有些年份还超过美国。
拉丁美洲和亚太区经济表现的不同,背后的原因很多,亦相当复杂。简单来说,首先是发展策略的不同。二战后至八十年代,拉美经济体比较多依靠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来发展国内产业,而亚太区则以出口导向为主。比较两种策略,后者更着重市场力量,汰弱留强、提升效率。
第二个主要分别,是拉丁美洲的宏观调控政策常有失误,导致通胀高企、汇率波动及债务危机等,给经济带来震荡和不确定性。虽然亚洲在上世纪末也出现过金融风暴,但总的来说,数十年来宏观经济的表现优于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胀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胀率比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高63%。
「华盛顿共识」推行自贸
说到拉丁美洲的宏观调控,自然要提及「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经济经历过数十年宏观失控的折腾、特别是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后,逐渐接受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 1989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项有关政策,并统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包括自由贸易、容许外资进入、国企私有化、保护产权、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及严谨控制政府财政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政策,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华盛顿共识这个名词去概括上述政策,但这个名词很快就变成指导性的,即经济发展必须依据这些政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共识」似乎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后,由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跟从「华盛顿共识」,有外国学者抛出「北京共识」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政策,但中国政府和学界都不用这个名词。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经济或许比以前采用更多有关的建议。比如开放贸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贸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东亚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国维持原有的差距,即长期停留在美国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发展策略和宏观调控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还受制于很多其他因素,如区内的整合不足、出口产品单调、强烈的民粹主义、严重的收入不均等。迈入2023年,在众多负面因素下,全球经济不容乐观,在缺乏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拉丁美洲亦难独善其身。
【注】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