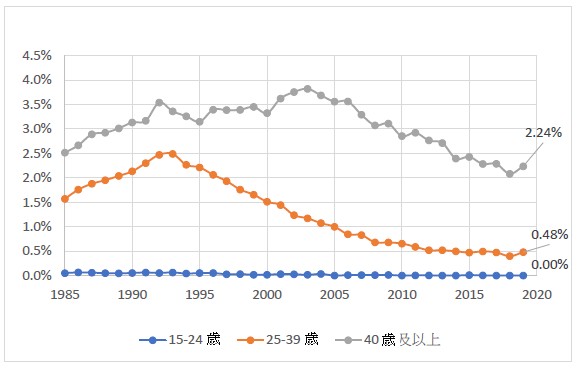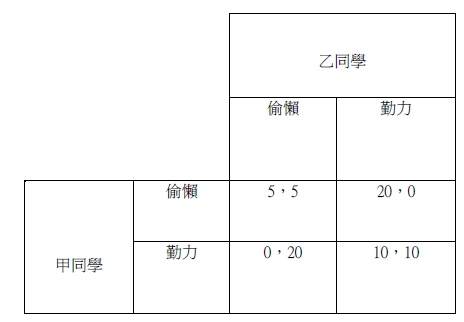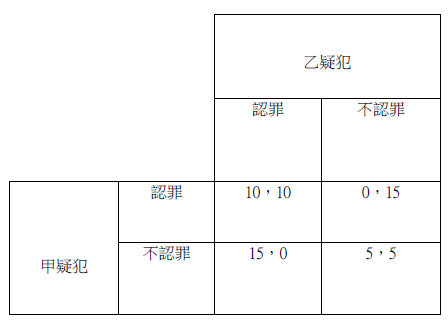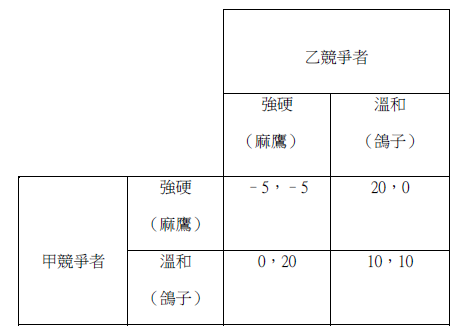港深合璧的協同效應
港深合璧的協同效應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提及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及其在大灣區的領導地位將更提升,卻無觸及香港對深圳及全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有人認為這等於將香港邊緣化;其實香港在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軌跡中,一直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港商早期已在當地投資,時至今日,香港特區仍然是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在當地經營的香港企業為數共約8萬【註1】。
正當國家面對嚴峻國際局勢、本港經濟持續衰退,評論與其突顯港深之間競爭,不如聚焦香港如何繼續借助「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與深圳進一步攜手合作,在大灣區發展互補共榮。
締造奇蹟的要訣
從1970年代末一個華南市鎮發展成今日的國際大都市,深圳是國內經濟特區成功實踐的表表者。2019年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達2.7萬億元人民幣,在亞洲城市中領先香港一位,名列第五,堪稱「偉大奇蹟」。
習近平就改革開放後累積的經驗,總結新時代經濟特區的成功關鍵,在於「十個堅持」。配合堅持發展的大方向,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創新在驅動經濟增長擔當的角色日形重要,筆者早前已在本欄先後撰文探討【註2】,在此不贅。創新有賴人才,重點包括發展策略性新興產業、數碼經濟等。除了基礎研究和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方面,還須加強金融、研發、設計、會計、法律、會展等現代服務業,提升業界競爭力。同時應適當地放寬人才政策,引進並培養所需人才和創新團隊。
此外,必須致力全面對外開放,首要條件是提高對海外投資者「引進來」的吸引力和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競爭力。強化吸引力方面,須在社會上提供法制保障、文化生活、交通設施、資訊自由,保持資金流通和政治穩定。要提高競爭力,除了着眼於價格和品質,還須在創新應用層面上不斷突破,兼顧科技與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創新足以帶領世界生活潮流,從而提升中國產業及服務在國際上的需求。經濟發展新格局並不局限於國內循環,而是國內國際雙循環。增強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將有利於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
雙城經濟的幾何級數升勢
圍繞着珠江三角洲的大灣區涵蓋多元化的綜合發展,可容納各類商貿或專業服務在區內落戶。粵港澳經濟運行的規則機制銜接,則有助促進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以及乘客、貨物便捷流動。至於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改革開放、落馬洲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的規劃,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建設,也一一蓄勢待發。
香港、深圳一衣帶水,在地緣經濟環境中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習近平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只要協調相互衝突的利益關係,令市場、產業和基礎設施一體化,港深就能共享資源和產業分工,提升整體的競爭力;透過啟動雙引擎功能,不但兩地雙贏,大灣區發展定將更上層樓。
內外變局中的新部署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歐美政府即使紛紛實行低利率量寬政策,仍難免瀕臨經濟危機邊緣,亦不排除會因另一次金融危機而陷入經濟蕭條。正當世界處於動盪變革期,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則乘勢而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全球經濟、科技、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大幅調整。
中國經濟則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提高,經濟長期向好,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正邁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嶄新發展。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香港有何經濟角色?
回歸以來,香港發展既一直獲得國家大力支持,而大灣區發展計劃對推動區內各類產業(如高等教育、環保綠化工程、醫療衞生、創意文化)都具前瞻性的指引作用,無疑為香港帶來不可多得的歷史性契機。
至於以創新為核心的未來發展方向,香港2018年投放於研發的整體開支,只佔GDP約0.86%,遠低於經濟發達地區的2.4%。既然香港亟待通過創新和科技提升自身競爭力,特區政府應借助深圳在科研和創新的優勢,從而更全面配合國家的策略性發展方向。
釋放港深融合的龐大潛能
在人才資源開發方面,香港各高等院校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已成為亞洲區內一大高等教育中心,在不少學科以及基礎研究領域上都居於世界前列。培訓人才方面,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為例,回歸後通過與上海、北京的重點大學所合辦的課程,在深圳、北京和上海培訓與時並進的領導人才。
港深可在大學教育上合作,以提供更多機會讓兩地學生互相學習,透過交流和實習計劃,增強香港學生的專業知識之餘,亦深化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
事實上,特區政府提供資助計劃,鼓勵香港青年創業者發掘在大灣區發展的機會,至今已有青年初創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享有特殊地位及許多不可替代的優勢,如「普通法」法制、資訊自由、言論自由、資金出入自由、自由貿易港定位等,在金融、物流及各類專業服務行業別具競爭條件,足以在國際上發展成知識及學術中心,吸引各地人才來港,接受在中國營商的各項相關專業培訓,並從中向中國經濟取經。深圳現執國際科研牛耳,香港則具備豐富環球專業管理及融資經驗,兩地可望在「科技創新管理及融資」領域踏上新合作台階,讓香港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打造更大發展空間。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國際大都會,香港憑藉自身條件和經驗,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與內地城市和國際城市的連通性,充當面向海外市場的超級聯繫人,為大灣區的發展引進資金、人才、技術及國際經驗,而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環,亦將能繼續發揮所長,有所貢獻。
註1:行政長官出席香港中華總商會120周年會慶酒會致詞,2020年10月15日
註2:2020年7月29日〈經濟洗牌 以創為進〉,2020年9月30日〈創業脫貧 雙軌並行〉,謝國生,《信報》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廿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