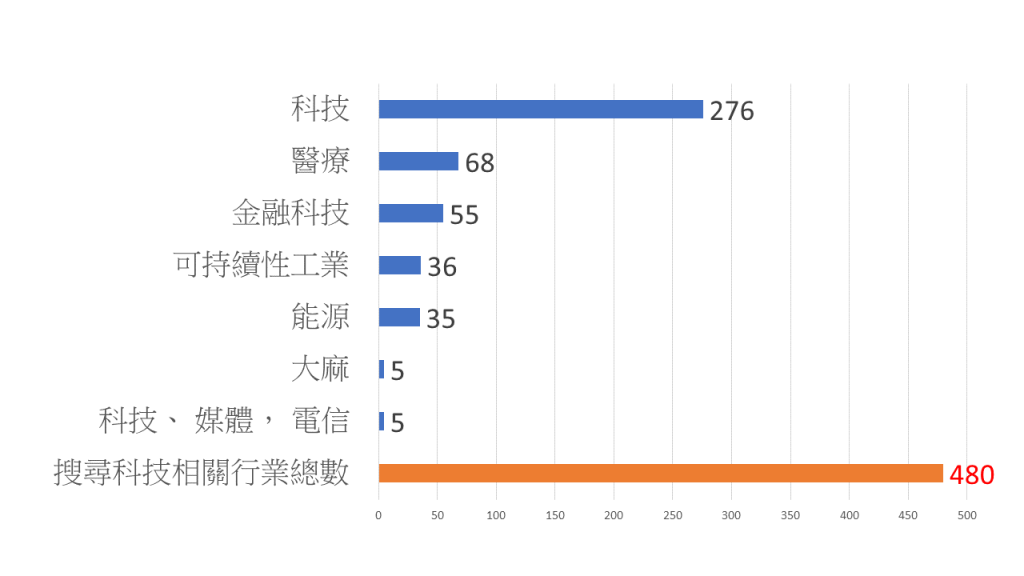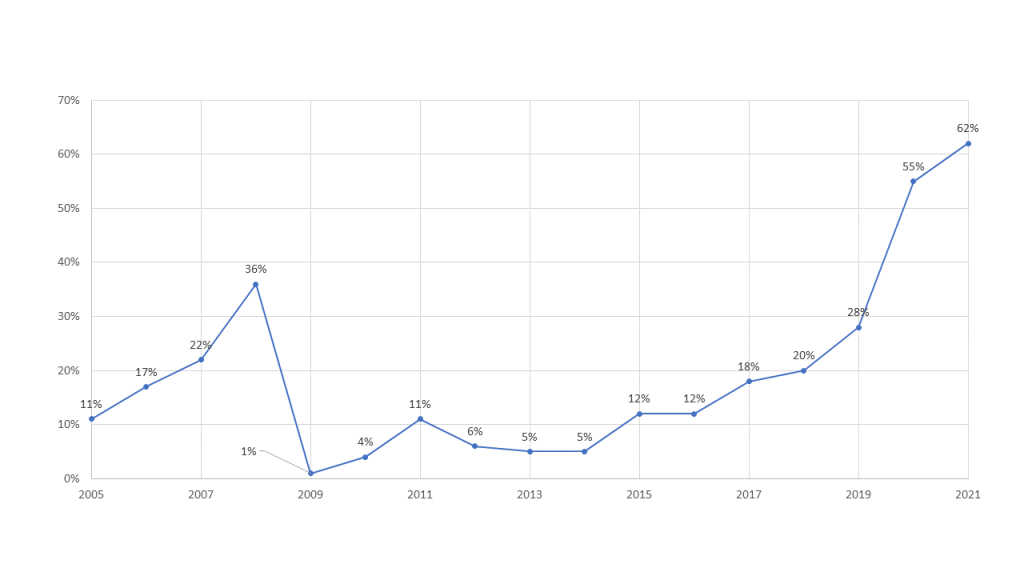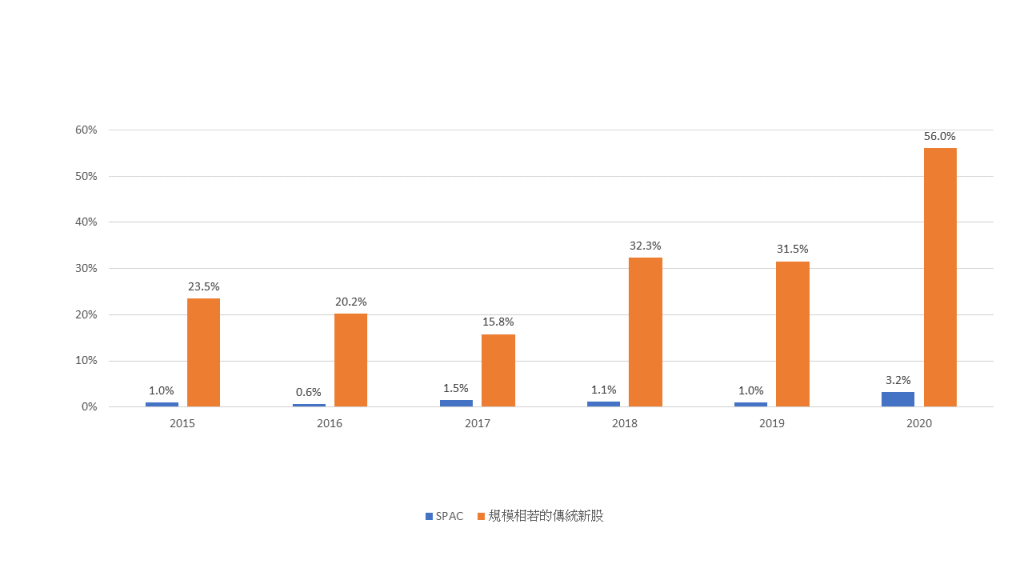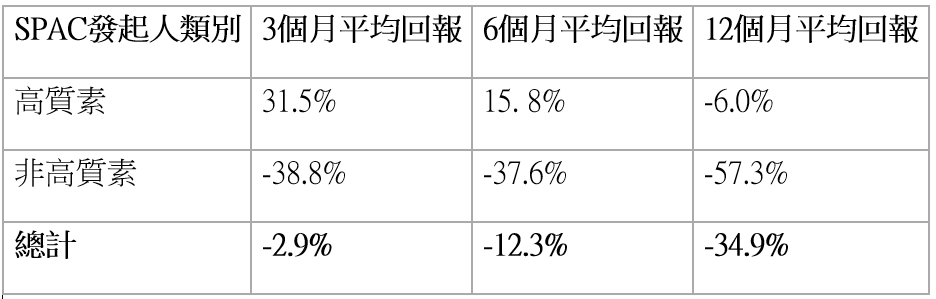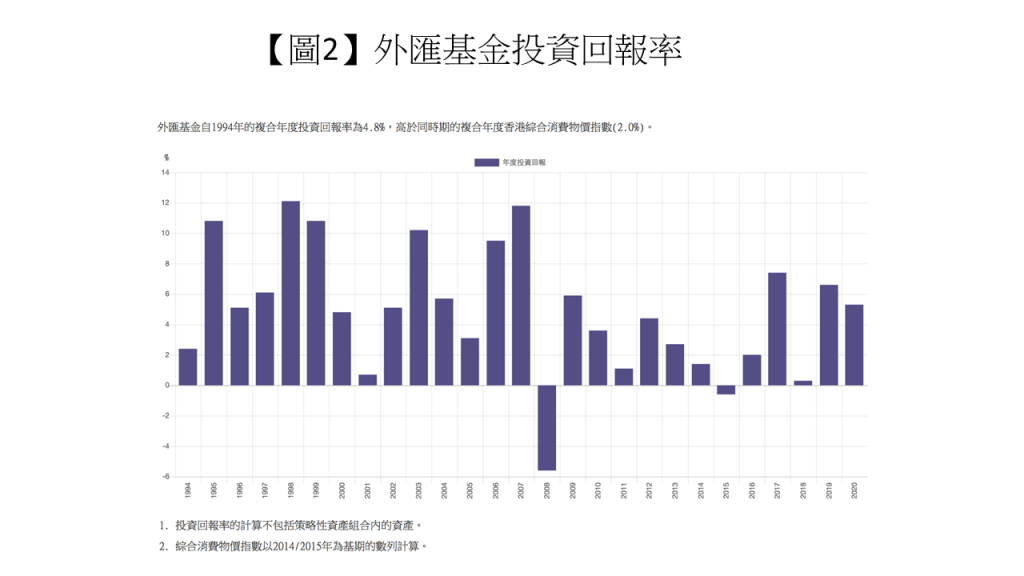後疫情時代的政策建議
迄今為止,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賴嚴格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來阻止病毒變種的流入,但我們建議政府,應提早研究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並根據研究制定相關政策,從而讓本港經濟得益。
不少國家已有類似的計劃,例如新加坡成立了一個後疫情經濟復甦工作組。該工作組由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Desmond Lee)和PSA國際集團首席執行官Tan Chong Meng擔任主席,帶領來自公私營部門的21名成員為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提出建議。其中包括反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並特別強調新加坡須保持對全球人才和技能開放的態度。
疫後復甦 人才爭奪戰
全球經濟正轉型為以知識和創新為主導,各個國家對具備合適技能和創造力的人才需求日益俱增,因此世界各地對人才的搶奪正在加劇。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於2019/2020年第二期的研究簡報中指出,香港的人才引進計劃成效並不理想。報告提及,香港的高生活成本削弱了其所支付的高薪的競爭力:若將不同地區的薪酬按匯率轉換成美元來進行對比,香港高級專業人士的年薪在國際上並不特別有吸引力;若以所在地區的生活成本為參考,香港的薪酬甚至比內地和新加坡同行低。另一個阻礙人才來港的原因是,香港在各項全球宜居性調查中總體得分不高。其他因素包括環境質素、生活質素以及外籍人士配偶和子女能獲得的支援。因此我們建議香港政府提出政策以增加房屋供應,從而控制樓價和租金。這不僅有助吸引更多專業人士來港,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亦有助降低在港營運公司的薪酬成本。
疫情也改變了市民的工作方式。例如,愈來愈多公司允許員工遠程工作(例如在家工作),這意味着企業在香港招聘時亦要把那些不願搬遷至香港的外地求職者考慮在內。因此,我們不難想像,港企需要和其他地區的對手(例如新加坡)爭奪這一類人才。遠程工作的普及將改變城市爭奪人才的方式。
在新常態下,政府必須制定具體政策吸引人才來港工作,因為以這種模式工作在某些行業很常見。政府也須決定應否吸納大量選擇居住海外的人才為香港公司工作。
目的導向監管策略
過去十年,日新月異的技術已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以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長足進步,加強了公司了解並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金融科技(FinTech)也顛覆了消費、傳統銀行業務、借貸和投資的運作方式。多年前政府出於善意而寫下的監管規則,到今時今日可能已成為絆腳石。因此,監管方式需要與時俱進。學院最近於《2021年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中,就強調了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制定以目的為導向(Fit-for-purpose)的監管法規的重要性。
據《南華早報》2019年3月21日的報道,2018年有關香港的士司機的投訴達到新高,超過11000宗,相較過去十五年多了超過一倍。我們認為,引入競爭可對的士司機施加壓力,是提高服務質素的有效途徑。儘管香港人口在過去26年增長了23.5%,但自1994年以來,香港政府並沒有頒發任何新的的士牌照,這意味着的士司機不需要改善服務質素,也能繼續接載乘客。若優步(Uber)等交通網絡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平台能進入市場,的士便需要面臨來自私家車的競爭。即使消費者委員會提出,「為了降低進入壁壘並促進創新,建議減少對網上叫車服務的規範要求。」但時至今日,私家車司機在香港提供收費服務仍屬違法。
為了增加的士與網上叫車服務之間的競爭,我們在政策綠皮書中提出的一項建議是,政府應出售經營交通網絡公司的特殊牌照,持有這類牌照的公司能合法地提供私家車乘車服務。為減輕它們與的士之間的衝突,政府可以限制每個公司旗下車輛的數目,每日乘車次數,或只允許旗下車輛於特定時間載客。銷售這些牌照的部分或全部收入可以轉給現有的士牌的持有者,以減輕這些公司對現有持牌人造成的損失。因此,網絡叫車服務所遇到的來自的士持牌人的阻力就會減少。如果交通網絡公司能為乘客和司機創造可觀的價值,那麼它們應在支付給予的士持牌人的補償後,依然保持盈利。筆者亦留意到近期,交通網絡行業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2021年8月20日,優步宣布收購香港的士應用程式,收購後優步同時為的士和私家車司機提供服務。
我們堅信交通網絡公司、的士行業相關人士和消費者之間存在三贏。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制定政策把交通網絡公司合法化及加以規管,而不是將此事無限期地擱置。我們意識到下一個顛覆性的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政府應該在其出現之前,在監管方式上做出變革。例如,近年來,愈來愈多患者使用遠程會診或在線醫療諮詢。儘管患者並非與醫護人員共處一室,但其體驗可能未必遜於當面會診。鑑於香港醫生短缺,愈來愈多患者可能會從香港以外的地區獲取遠程會診服務。因此,對於海外醫生通過互聯網向香港居民提供諮詢甚至開藥方是否合法的問題,政府應盡早研究並採取行動。
我們會在後續文章繼續探討後疫情時代與經濟復甦有關的話題,並根據我們的見解提出其他政策。我們希望我們的政策建議有助於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使本港經濟在疫情後強勁復甦。
參考:
Commonwealth Enterprise & Investment Council, “Singapore’s post-COVID-19 recovery plan and Commonwealth,” 24 May 2021
HKU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1
Mayur Shetty, “Solve. Care partners HealthLink to bring cross-border telemedicin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17 Sep 2021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2 2019 –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mplaints against Hong Kong’s taxi drivers hit record 11,000 in 2018 with bad driving, longer routes and overcharging among gripes,” 21 Mar 2019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