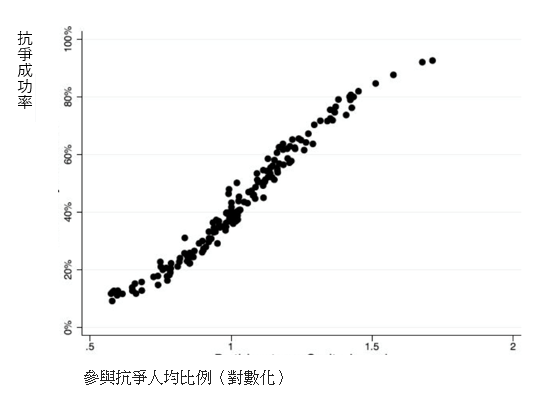The Path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
受當前政治事件影響,香港經濟已經進入技術性衰退,經濟困局近期只會愈發嚴峻。然而,香港經濟面臨的更大挑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前景不明朗。主要癥結在於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傳統產業增長乏力。唯有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才是香港經濟的唯一出路。
產業結構單一 增長動力不足
從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香港經濟增長顯著減速,年均生產總值(GDP)增速只有2.81%,遠低於1999年到2008年約4.72%的平均增速。香港經濟的增長表現,也明顯遜於同期新加坡的增長表現。同為外向型開放經濟,新加坡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率是4.68%,大幅拉大了與香港的差距。
香港經濟增長乏力,可以從產業結構看出原因。香港產業結構單一,農業和製造業在整個經濟中佔比微乎其微。四大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以及旅遊)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其增加價值佔本港生產總值(GDP)比重在2007年巔峰期高達60.3%, 近年有所下降但仍佔55%以上(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當中最重要的是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各佔21.5%和18.9% (2017年)。 這兩個外向型核心產業,帶動旅遊,零售和相關支援服務(如法律服務)產業的發展,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然而,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間,這兩個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和4.1%, 遠低於之前的增速,火車頭的拉動力顯著下降。
香港這兩個核心支柱產業,未來前景更不樂觀。一方面,反全球化趨勢在全世界愈演愈烈,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近年開始不增反降,未來相當長時間可能會持續惡化。同樣倚重(但不像香港般依靠)貿易和金融的新加坡, 過去兩個季度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反全球化的時代,香港的貿易和金融業要持續增長,無疑挑戰巨大。
另一方面,新的數碼革命浪潮中,一個重要的經濟趨勢是去中介化。這對以中介為基礎的香港核心支柱產業有深遠的影響。阿里巴巴集團去年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宣布,未來5年在電子商務的平台上將實現2千億美元的進口。京東也有類似的雄心勃勃的進口計劃。就如國內貿易和零售日益被電子商務取代一樣,越來越多的進口貿易以及相關的報關物流金融服務也將被電子商務主導。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如支付,轉賬,信用,信貸等等領域的電子化數碼化,理財和投資的人工智能化,無不是對傳統金融中介服務的衝擊。
由此可見,香港過於單一的產業結構現在已經疲態盡顯,而長遠來看,反全球化及去中介化趨勢的影響將使其更加難以為繼。香港需要加強支柱產業的競爭力,但更重要的任務是進行經濟結構轉型。
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 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
在考慮發展新的核心產業時,新產業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必須符合和依靠香港的比較優勢,能夠在全球競爭中佔據先機;第二,必須順應未來經濟社會和技術的潮流,有足夠大的市場需求,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持續的增長動力。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符合香港的比較優勢,但如上面分析所表明,未來需求在下降,增長空間有限。近年港府提出大力發展創科,扶持創新企業,發展人工智能等政策,這當然是順應未來潮流的應有之舉。然而,創科要形成推動香港經濟的核心產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現實的。香港在研發的投入只有GDP的0.8%,而發達經濟體的研發佔GDP的比重普遍超過3%。 在數碼革命時代中至關重要的數據,市場,人才方面,香港都沒有特別優勢,更不用說其它區域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先發優勢。
筆者認為,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應成為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早在2009年,香港政府曾經確定發展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以及醫療在內的六項產業為優勢產業,遺憾的是10年過去這項政策還未真正得以落實。
首先,香港在發展這些高端專業服務業上有獨特的優勢。香港的安全和法治,是這些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和便利的交通,是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天然優勢。這些產業有較高的技術門檻,而香港已經在這些領域建立了亞洲領先的地位,比如醫療和教育;或者有輝煌的傳統,如文創。關鍵是如何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把這些專業服務行業scale up,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動力。
其次,高端專業服務的國際市場前景廣闊,需求不斷擴大。有媒體報導並引用數據指出,全球醫療旅遊產業從2000年的產值不到100億美金,飆升到2017年的7000億美金,並且以每年20%的速度保持增長,已經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一個新興產業。以日本為例,高端醫療體檢,尤其是癌症的早期篩查與防治,預計吸引每年約31萬人次的僅以體檢為目的的中國遊客。在教育產業方面,國際教育作為澳洲第三大出口產業每年給澳洲創造近200億澳元的價值。尤其是澳洲公共教育通過留學產業化所創造的巨大收益得到極大的支持,使得教育資源更加豐富,這對公共教育資源緊張的香港也可作參考。同時,文創產業的全球產值也高達2.25萬億美元。
高端專業服務的產業化與公共服務的相互促進
發展高端醫療及教育產業是否會稀釋公共資源,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只要政府規劃得當,正確引導,醫療及教育產業化不僅不會與公共服務相衝突,反而能夠促進提升公共服務。
以醫療為例,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雖保障了市民以低廉價格享受優質醫療服務,但醫療從業人員不足,病床緊張,患者輪候時間長等問題愈來愈惡化。政府醫療開支雖逐年增加,但佔GDP比重僅約為5.5%至5.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如何在財力可持續的條件下擴大醫療供給能力,同時又不降低醫療專業人才的收入和激勵,一直是困擾香港醫療制度的難題。通過發展高端醫療產業,從需求端開放,引導私人資本和政府投資共同作用,是增加醫療供給能力,提升醫療公共服務的解決之道。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公共服務上是相對落後的。目前全港每年只有15000位本地生受資助學額進入公立大學,佔應屆青年的25%左右,而世界上其它發達經濟體70%的年輕人可享高等教育。政府應採取一系列政策,把本地入學名額盡快提高到50%。短期內大幅增加本地學額,只靠公共財政會令財政支出面臨過大的壓力。參考澳洲經驗,利用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高水準的優勢,吸引適量的非本地學生自費留學,從而增加本港學校教育經費,增加教學資源,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制度創新和妥善規劃是關鍵
高端專業服務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推動,需要公共資金和社會資本的共同作用。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妥善規劃,穩妥有序的擴大供給能力,保障公共服務水平穩步提升。
制度創新是釋放供給能力的關鍵。醫療服務的供給能力提升,需要加強本地醫學教育培育人才的能力,准入規則和條件也必須逐步放鬆。國際需求的導入,私立醫院的建設,醫護體系的配套,醫師資質的放鬆,在政府協調下同步推進,就能不斷提升供給能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學人員延遲退休可以在短期內補充現有教學資源。增加教育研究經費,同時改善經費的分配使用規則以提升公平性和資源效率,加上有序增加自費留學,便可逐步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香港文創產業要恢復往日的輝煌,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同時創造環境,促進文創繁榮的良好生態。
蔡洪濱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